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卷首语
卷首语 | 卷首语
-

小说 | 青山如黛
小说 | 青山如黛
-
小说 | 微芒汇作银河 (创作谈)
小说 | 微芒汇作银河 (创作谈)
-
小说 | 骑车男孩
小说 | 骑车男孩
-
小说 | 租客
小说 | 租客
-
小说 | 小红花
小说 | 小红花
-
小说 | 停潮
小说 | 停潮
-
小说 | 阿清
小说 | 阿清
-

诗歌 | 收脚印的人
诗歌 | 收脚印的人
-
诗歌 | 另一个你
诗歌 | 另一个你
-
诗歌 | 丢手绢
诗歌 | 丢手绢
-
诗歌 | 在大海里,度量从来都是用海水
诗歌 | 在大海里,度量从来都是用海水
-
诗歌 | 山把路举在醒目处
诗歌 | 山把路举在醒目处
-
诗歌 | 廊桥之上
诗歌 | 廊桥之上
-
诗歌 | 停止答题
诗歌 | 停止答题
-

散文 | 蕉叶白
散文 | 蕉叶白
-

散文 | 中山路的老时光
散文 | 中山路的老时光
-
散文 | 银魅
散文 | 银魅
-
散文 | 站在院子里看鸟
散文 | 站在院子里看鸟
-
散文 | 巡山记
散文 | 巡山记
-
散文 | 岛上木麻黄
散文 | 岛上木麻黄
-
散文 | 奔跑之于我
散文 | 奔跑之于我
-
散文 | 春山醒
散文 | 春山醒
-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滴滴司机笔记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滴滴司机笔记
-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河石记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河石记
-
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心愿
新大众文艺之窗 | 心愿
-
文艺探索 | 谢冕散文中的 “诗”与“真”
文艺探索 | 谢冕散文中的 “诗”与“真”
-
文艺探索 | 超现实、都市奇幻与新港风写作
文艺探索 | 超现实、都市奇幻与新港风写作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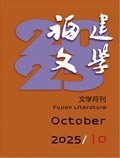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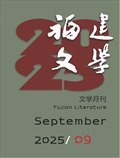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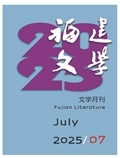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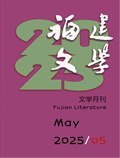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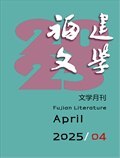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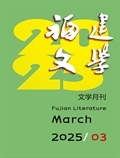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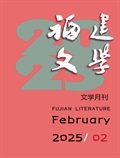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