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卷首语
卷首语 | 卷首语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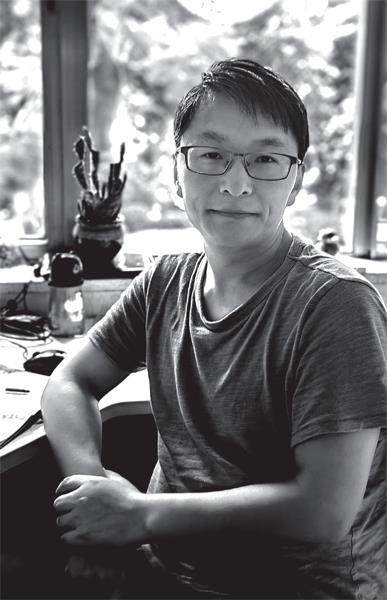
小说 | 幽野
小说 | 幽野
-
小说 | 我们写作的进与退
小说 | 我们写作的进与退
-
小说 | 极限下水
小说 | 极限下水
-
小说 | 遥不可及
小说 | 遥不可及
-
小说 | 高校往事
小说 | 高校往事
-
小说 | 甲壳虫
小说 | 甲壳虫
-
海洋文学小辑 | 半岛回音
海洋文学小辑 | 半岛回音
-
海洋文学小辑 | 马可·波罗和曾巩在闽海
海洋文学小辑 | 马可·波罗和曾巩在闽海
-
海洋文学小辑 | 你用了多少词折腾大海
海洋文学小辑 | 你用了多少词折腾大海
-
海洋文学小辑 | 大海,拥有无数的分身
海洋文学小辑 | 大海,拥有无数的分身
-
海洋文学小辑 | 海的回声
海洋文学小辑 | 海的回声
-

诗歌 | 必有人重写大海(组诗)
诗歌 | 必有人重写大海(组诗)
-
诗歌 | 峡河上的野麻鸭
诗歌 | 峡河上的野麻鸭
-
诗歌 | 我知道那些深情的摇曳
诗歌 | 我知道那些深情的摇曳
-
诗歌 | 小草星星点点的花格外不起眼
诗歌 | 小草星星点点的花格外不起眼
-
诗歌 | 霞浦忆(组诗)
诗歌 | 霞浦忆(组诗)
-

散文 | 橘录
散文 | 橘录
-
散文 | 门
散文 | 门
-
散文 | 暗隙有光
散文 | 暗隙有光
-
文艺探索 | 味觉史诗中的家国叙事
文艺探索 | 味觉史诗中的家国叙事
-
文艺探索 | 历史的在场与精神的返乡
文艺探索 | 历史的在场与精神的返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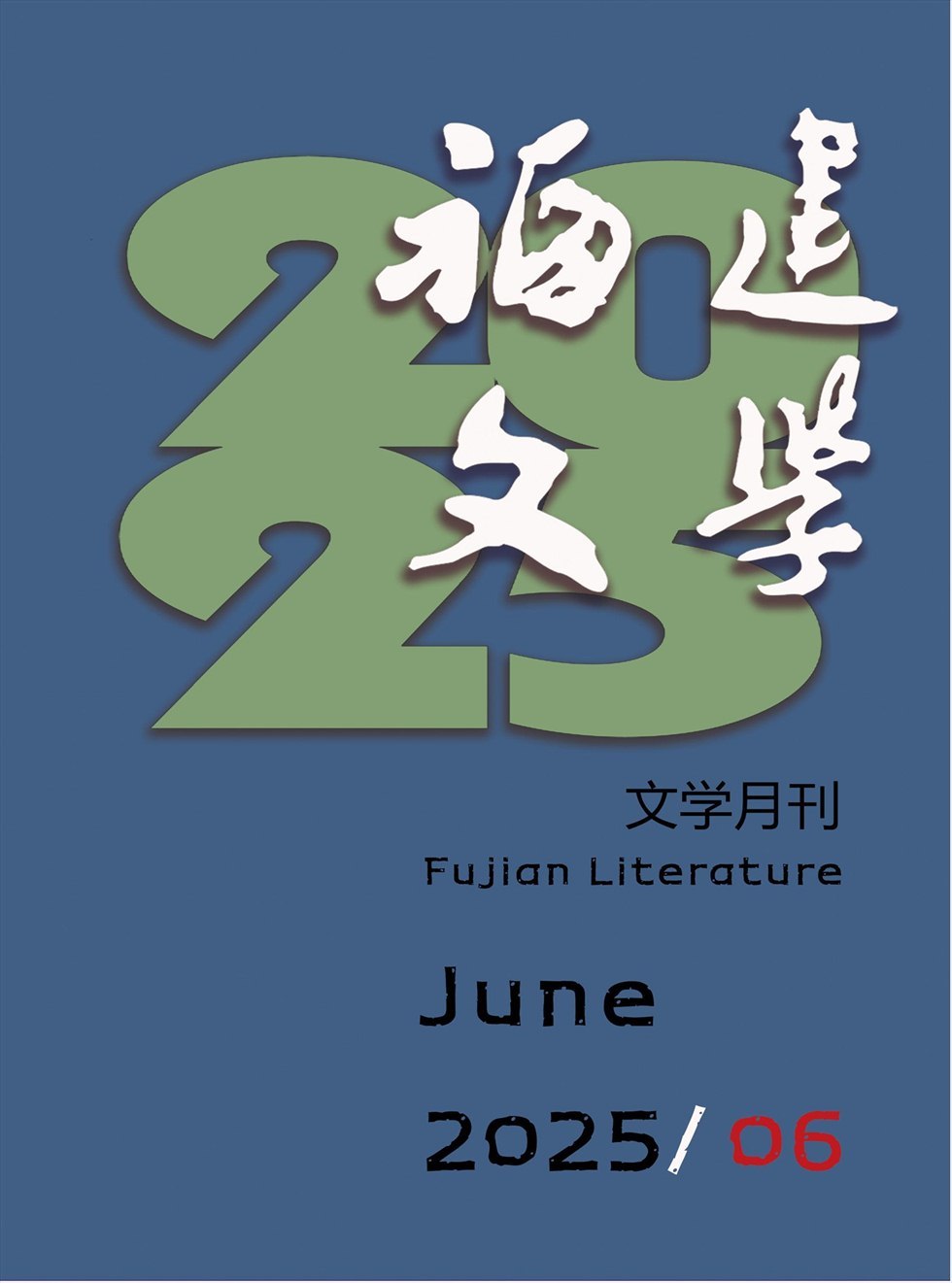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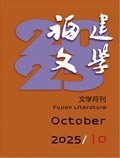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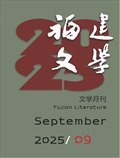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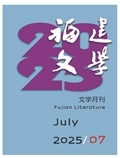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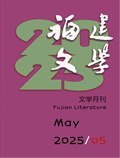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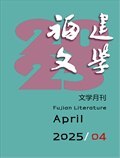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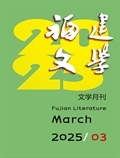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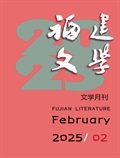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