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卷首语 | 卷首语
卷首语 | 卷首语
-
| 流水月光
| 流水月光
-
| 皖南夜谈
| 皖南夜谈
-
| 闻学散步
| 闻学散步
-
| 风筝吟
| 风筝吟
-
| 江流天外
| 江流天外
-
百花·自然书写 | 从大海到人海 【上】
百花·自然书写 | 从大海到人海 【上】
-
生活志 | 今夜何处宿
生活志 | 今夜何处宿
-
生活志 | 陆城粮仓记
生活志 | 陆城粮仓记
-
解释与重建 | 莱菔天涯
解释与重建 | 莱菔天涯
-
解释与重建 | 唇读
解释与重建 | 唇读
-
行旅 | 书香竹影水云心
行旅 | 书香竹影水云心
-
行旅 | 瘦西湖·江南梦
行旅 | 瘦西湖·江南梦
-
闲话 | 乡草二题
闲话 | 乡草二题
-
闲话 | 偏方
闲话 | 偏方
-

看·听·读 | 旧梦连环·叶家样
看·听·读 | 旧梦连环·叶家样
-
专栏 | 落木
专栏 | 落木
-
专栏 | 另一个季节的幽独 【下】
专栏 | 另一个季节的幽独 【下】
-

专栏 | 卷舒开合任天真
专栏 | 卷舒开合任天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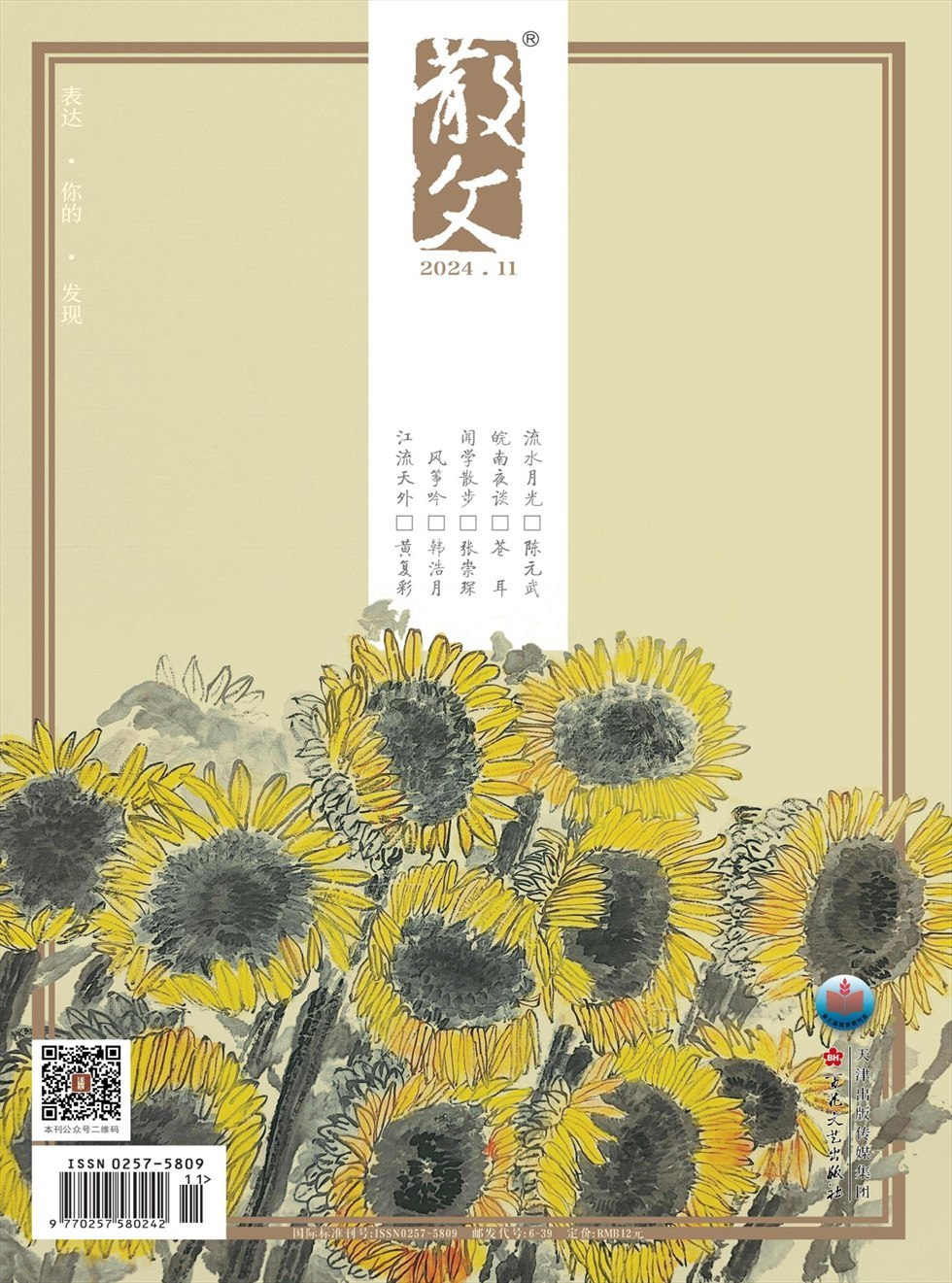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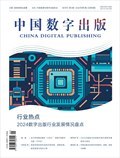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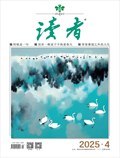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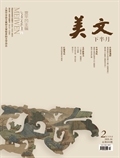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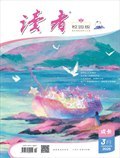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