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|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涵
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|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涵
-
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|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指向、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求
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|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指向、核心要义及实践要求
-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《南赣乡约》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《南赣乡约》重新认识和深入研究的问题
-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民生、人伦与性命:王船山对民心问题的阐释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民生、人伦与性命:王船山对民心问题的阐释
-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裴休的儒释会通思想研究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| 裴休的儒释会通思想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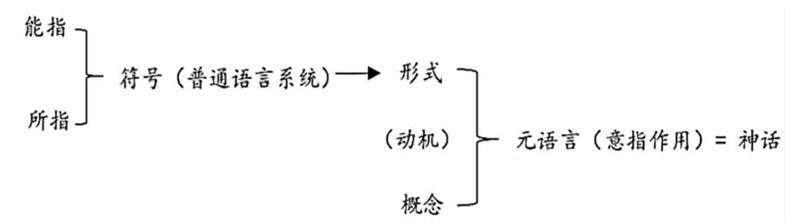
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“三大体系” | 神话学介入“文明连续性”命题的理论与实践
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“三大体系” | 神话学介入“文明连续性”命题的理论与实践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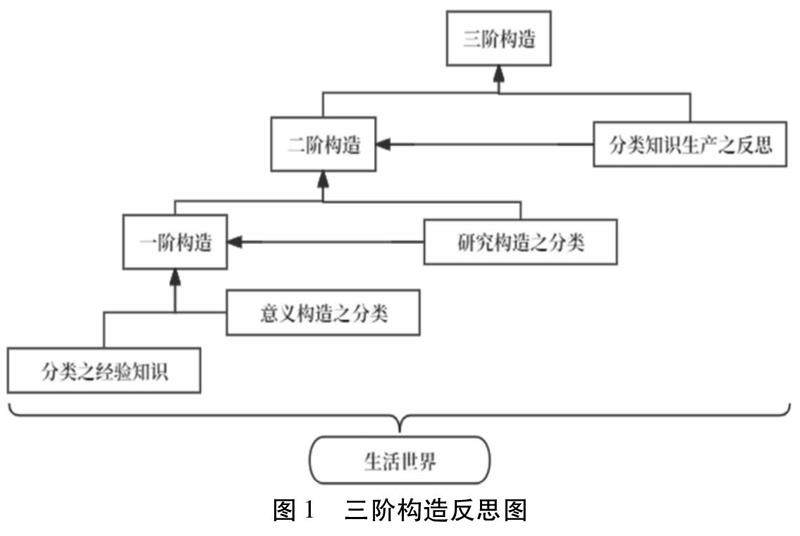
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“三大体系” | 关系、结构与秩序:费孝通分类思想研究
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“三大体系” | 关系、结构与秩序:费孝通分类思想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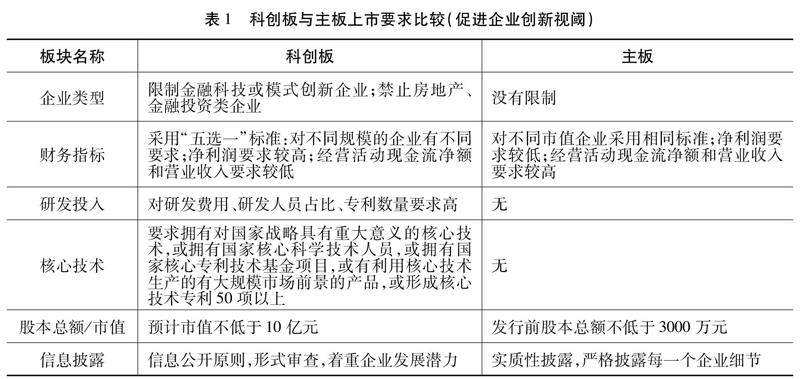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科创板提升了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吗?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科创板提升了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吗?
-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新型举国体制助推科技创新的实现机制:基于中国高铁发展的分析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新型举国体制助推科技创新的实现机制:基于中国高铁发展的分析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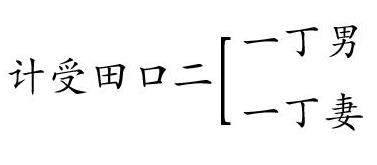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北魏孝文帝定民户籍及其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影响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北魏孝文帝定民户籍及其对推进社会改革的影响
-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融汇经例的史学:刘知几史学思想视域中的《春秋》经传史观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融汇经例的史学:刘知几史学思想视域中的《春秋》经传史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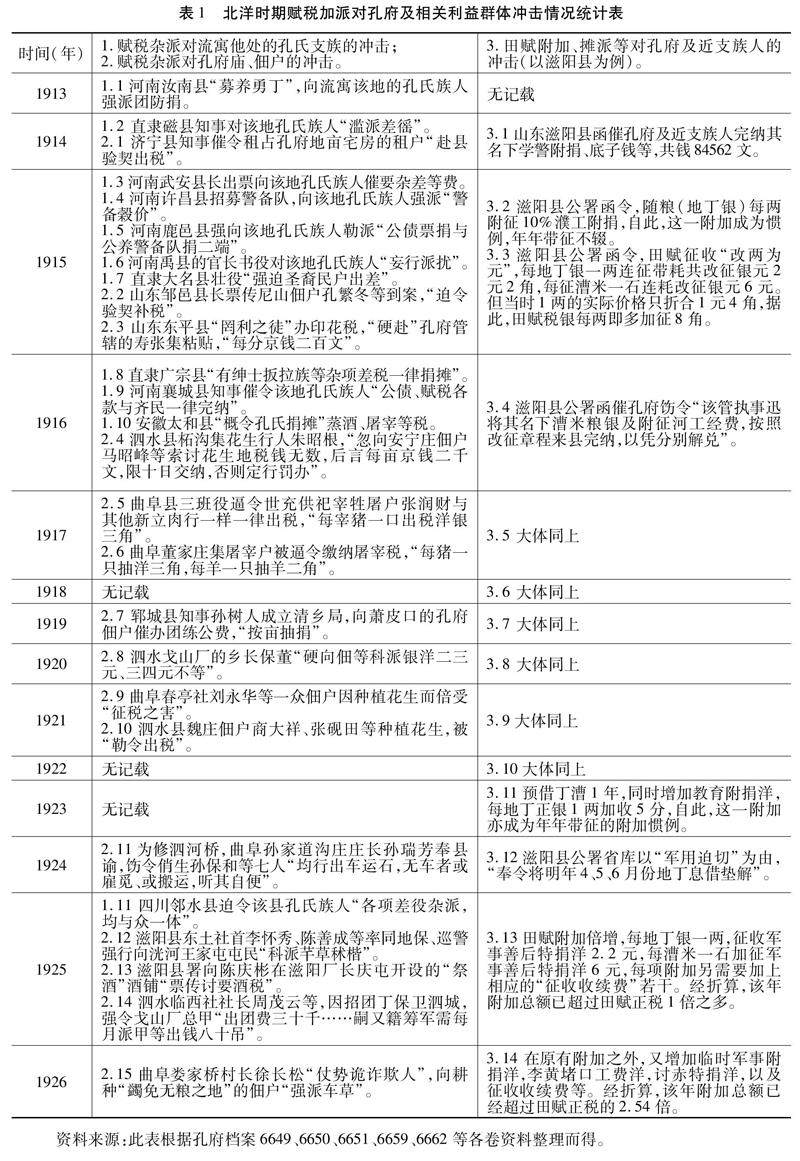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北洋时期赋税加派与孔府差徭优免权的终结
科技创新机理与实践 | 北洋时期赋税加派与孔府差徭优免权的终结
-
延安文艺研究 | “融”与“变”
延安文艺研究 | “融”与“变”

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