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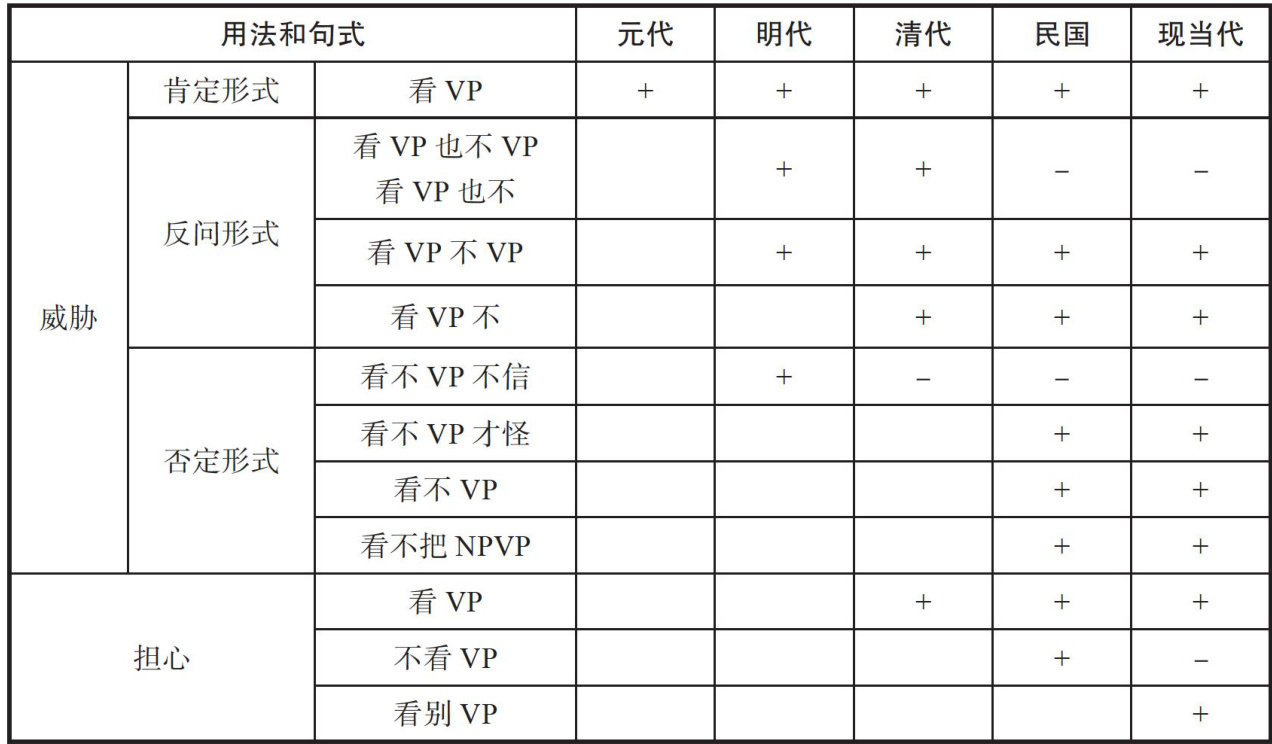
特稿 | “看VP”句式的否定羨余现象
特稿 | “看VP”句式的否定羨余现象
-
特稿 | 数字时代的辞书形态与功能
特稿 | 数字时代的辞书形态与功能
-
特稿 | 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二版“大”部的修订特色研究
特稿 | 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二版“大”部的修订特色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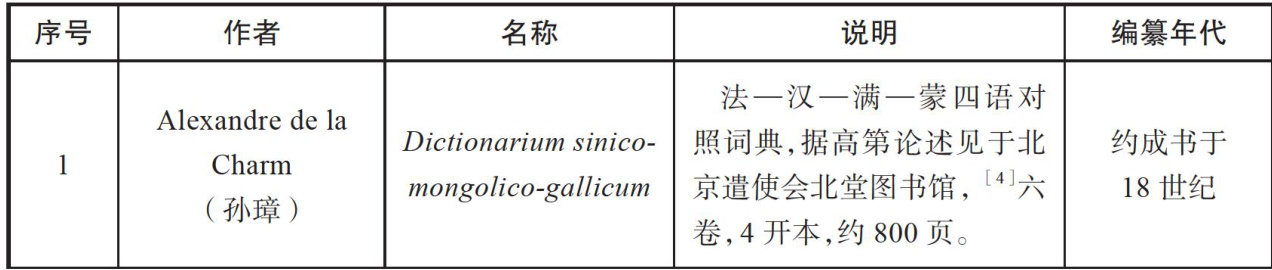
特稿 | 17—20世纪汉法双语辞书发展述评
特稿 | 17—20世纪汉法双语辞书发展述评
-

特稿 | 宋跋本为王仁胸《刊谬补缺切韵》抄本考(上)
特稿 | 宋跋本为王仁胸《刊谬补缺切韵》抄本考(上)
-

特稿 | 再论动词能否做定语
特稿 | 再论动词能否做定语
-

特稿 | 语体正式度的历时差异
特稿 | 语体正式度的历时差异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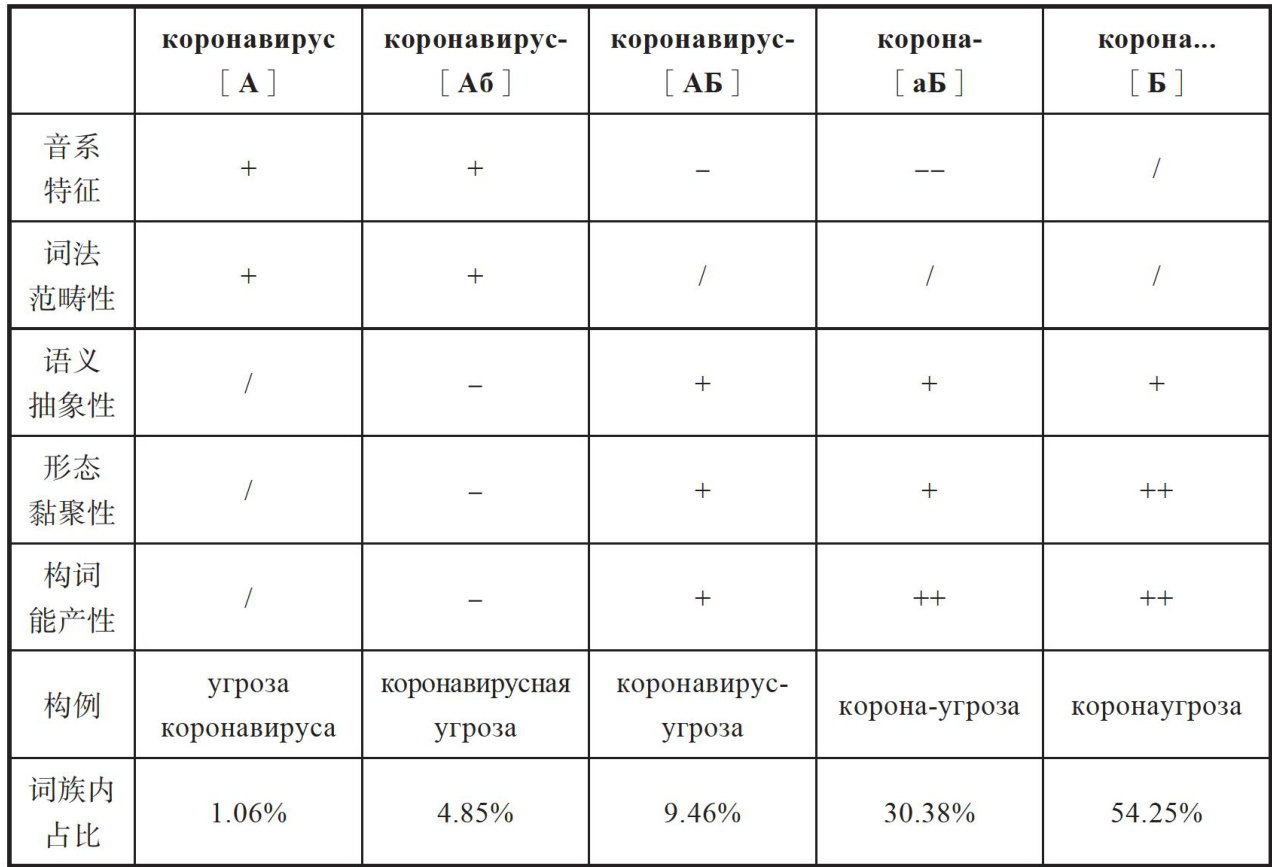
特稿 | 基于语法化理论的俄语类词缀研究
特稿 | 基于语法化理论的俄语类词缀研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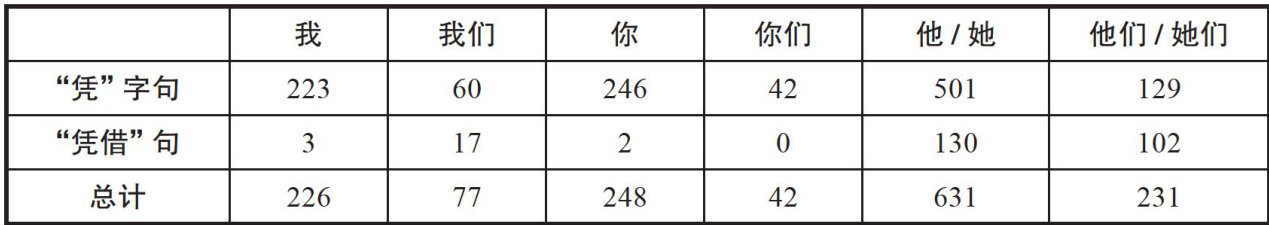
特稿 | “凭借”“凭”和近义介词辨析
特稿 | “凭借”“凭”和近义介词辨析
-

专栏 说字解词 | 休
专栏 说字解词 | 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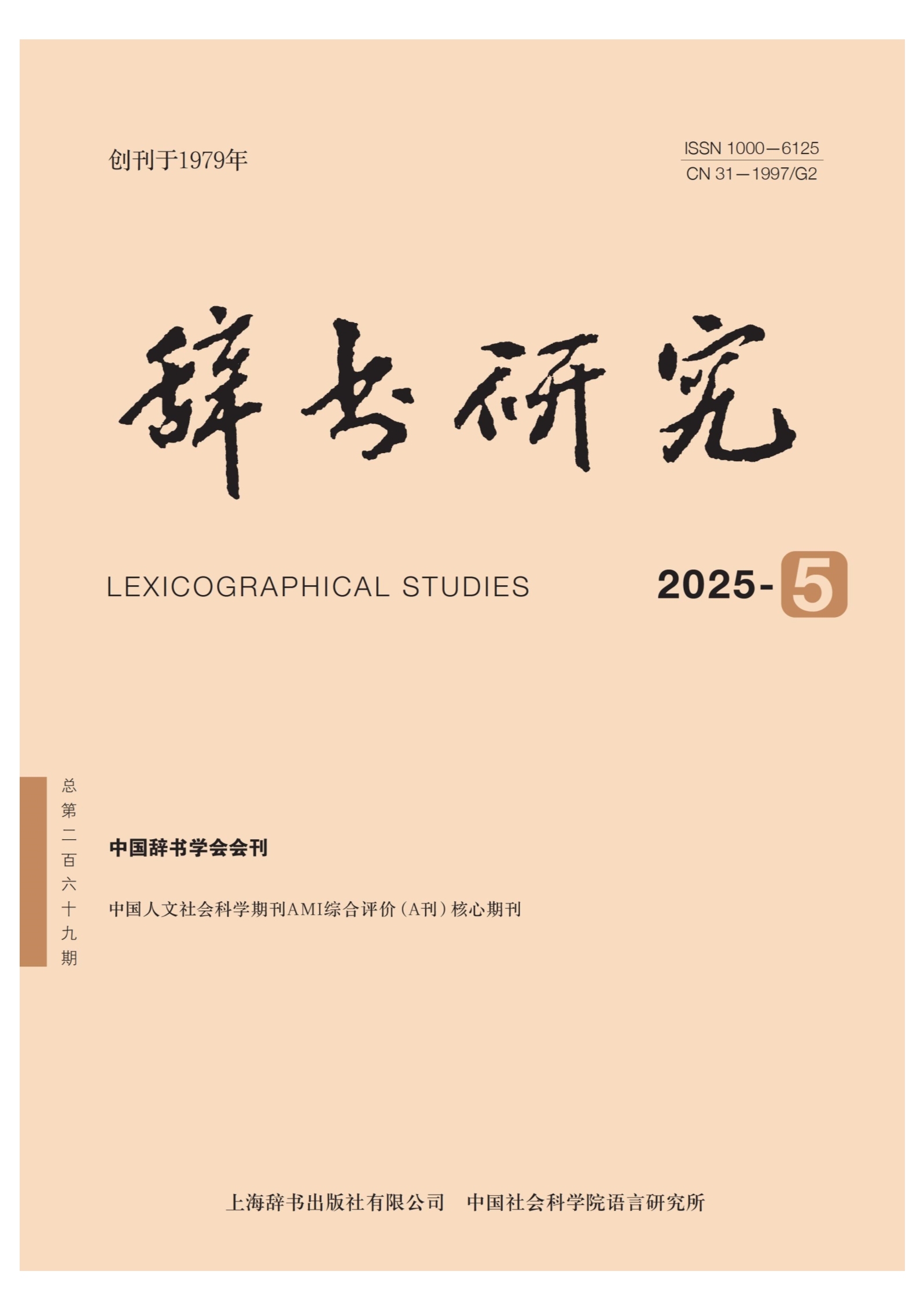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