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生活艺术/
- 视野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
导读 | 导读
导读 | 导读
-

视点 | 文艺复兴,打破了科学和艺术的鸿沟
视点 | 文艺复兴,打破了科学和艺术的鸿沟
-

视点 | 五个关键词,读懂文艺复兴
视点 | 五个关键词,读懂文艺复兴
-

视点 | 他画出了第一张自画像
视点 | 他画出了第一张自画像
-

视点 | 达·芬奇的10个发明
视点 | 达·芬奇的10个发明
-

视点 | 但丁:第一个现代人
视点 | 但丁:第一个现代人
-

视点 | 做一个为“美”落泪的人
视点 | 做一个为“美”落泪的人
-

大学之大 | 为什么要上一所好大学
大学之大 | 为什么要上一所好大学
-

大学之大 | 30岁以后,我需要一种社会认同感
大学之大 | 30岁以后,我需要一种社会认同感
-

大学之大 | 我教AI回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
大学之大 | 我教AI回答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
-

美育 | 为什么《红楼梦》要从神话写起?
美育 | 为什么《红楼梦》要从神话写起?
-

美育 | 树会记住很多事
美育 | 树会记住很多事
-

美育 | 写字
美育 | 写字
-

美育 | 商青铜鸮卣
美育 | 商青铜鸮卣
-

美育 |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
美育 |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
-

美育 | 南宋·雪树寒禽图
美育 | 南宋·雪树寒禽图
-

美育 | 名称
美育 | 名称
-

美育 | 真正的妖孽
美育 | 真正的妖孽
-
美育 | 刹那的人生
美育 | 刹那的人生
-
美育 | 月迹
美育 | 月迹
-
美育 | 混沌中的一瞥
美育 | 混沌中的一瞥
-

生涯 | 我最初的人生思索
生涯 | 我最初的人生思索
-

生涯 | 当我不再想让人变美
生涯 | 当我不再想让人变美
-

生涯 |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
生涯 |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
-

通识 | 学《诗经》注定要虎头蛇尾吗?
通识 | 学《诗经》注定要虎头蛇尾吗?
-

通识 | 游戏无法找到“金羊毛”
通识 | 游戏无法找到“金羊毛”
-

通识 | 王戎:知交半零落
通识 | 王戎:知交半零落
-

教与学 | 高中文科老师,开始无人可教
教与学 | 高中文科老师,开始无人可教
-

教与学 | 杜甫写花,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?
教与学 | 杜甫写花,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?
-

教与学 | 你要明白,有些事孩子真做不到
教与学 | 你要明白,有些事孩子真做不到
-

教与学 | 我喜欢的老师
教与学 | 我喜欢的老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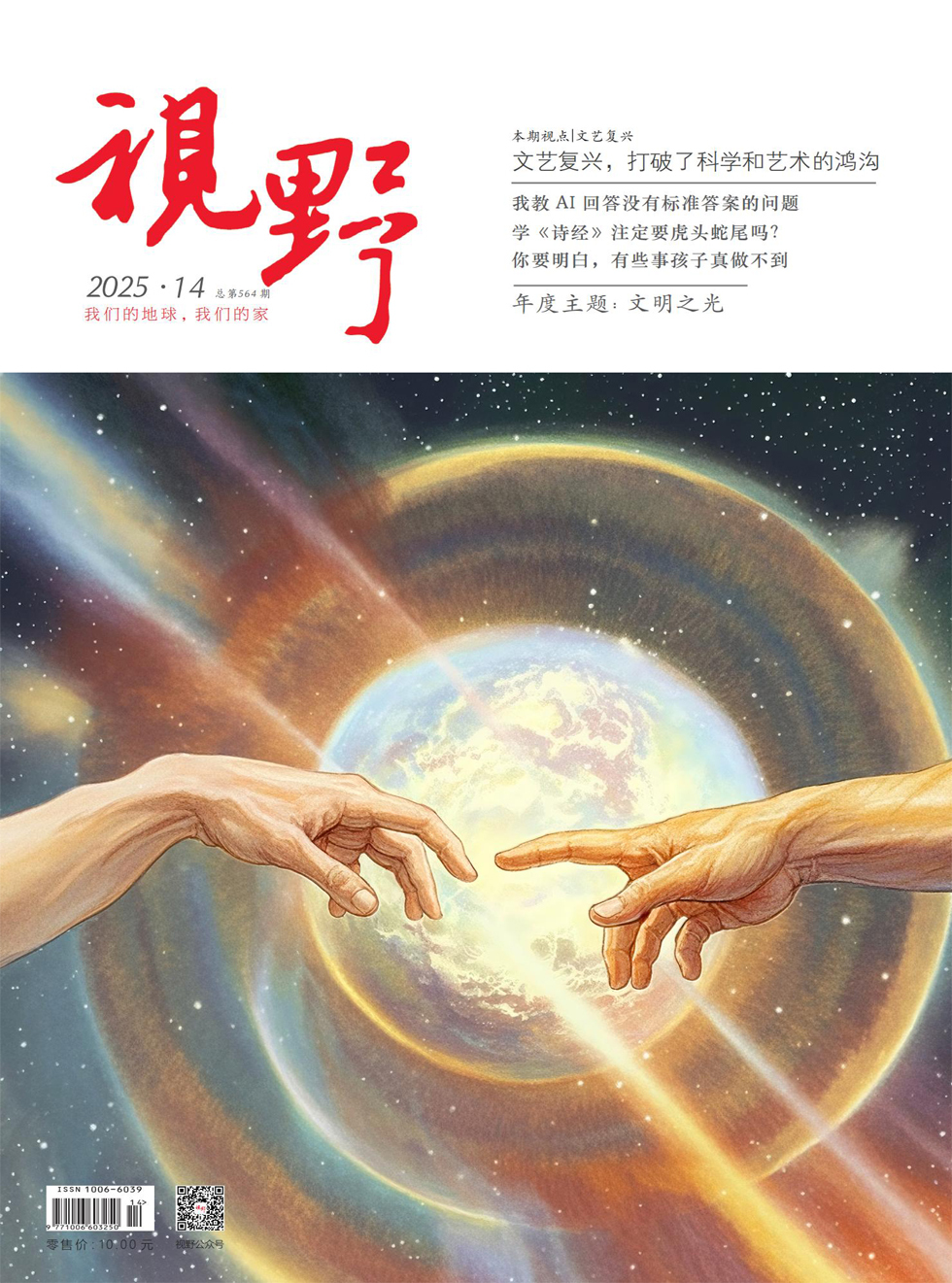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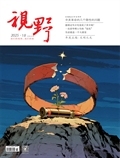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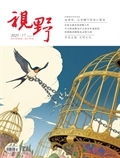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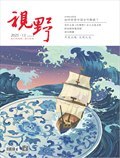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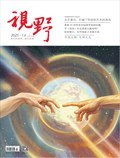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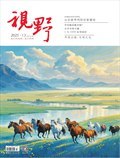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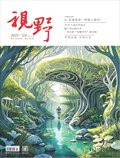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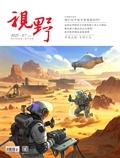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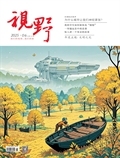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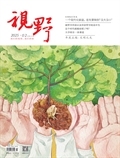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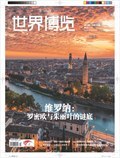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