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全部分类/
- 科学普及/
- 创新科技
 扫码免费借阅
扫码免费借阅
目录
快速导航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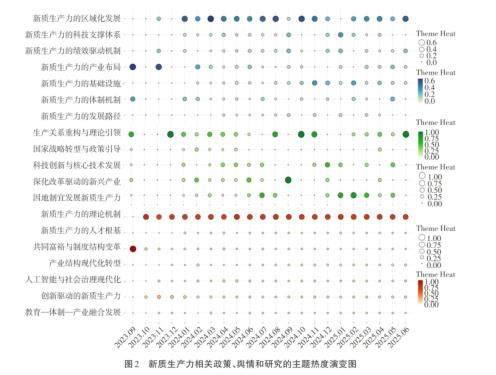
“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专栏 | 数据循证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
“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专栏 | 数据循证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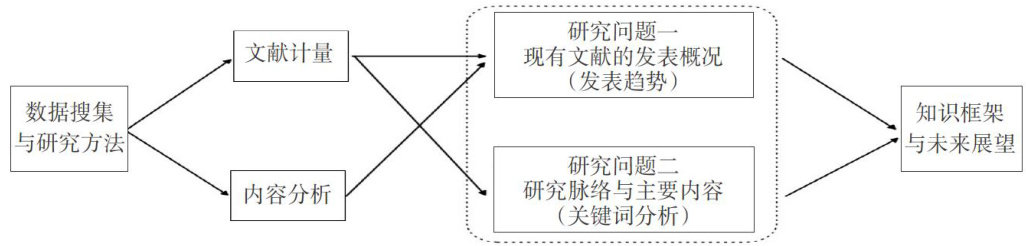
“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专栏 | 数智技术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:文献综述与知识框架
“新质生产力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”专栏 | 数智技术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:文献综述与知识框架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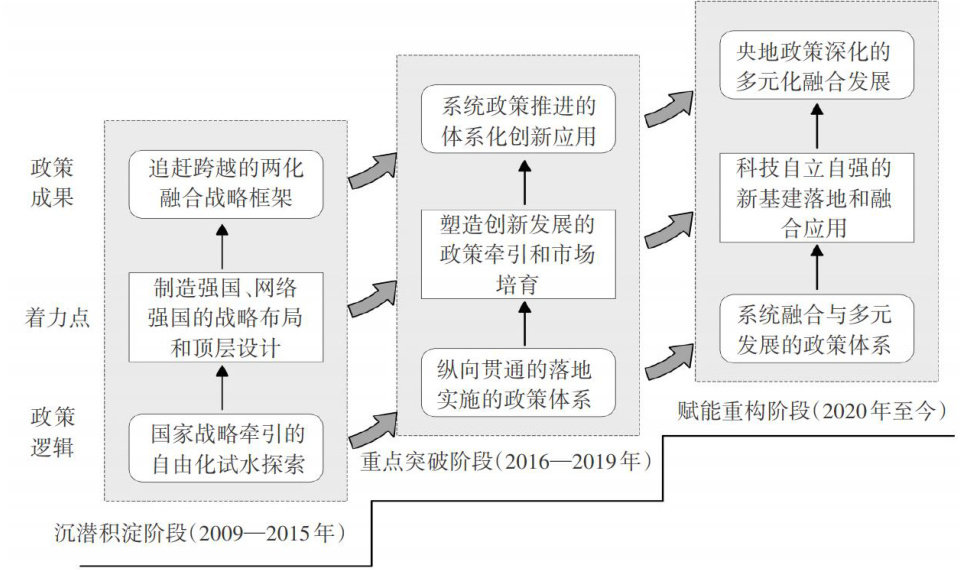
科学学理论与方法 |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阶段、演进机制及特征研究
科学学理论与方法 |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阶段、演进机制及特征研究
-

科技战略与政策 | 会聚视角下ICT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特征与突破路径
科技战略与政策 | 会聚视角下ICT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特征与突破路径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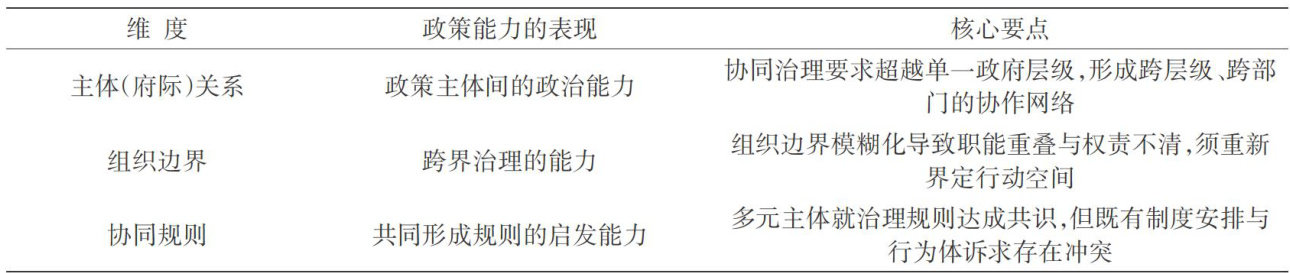
区域科技与创新 | “揭榜挂帅”攻关制度的多元模式:基于浙江实践的多案例研究
区域科技与创新 | “揭榜挂帅”攻关制度的多元模式:基于浙江实践的多案例研究
-

产业技术进步 | 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障碍因素分析
产业技术进步 | 科技创新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障碍因素分析
-

产业技术进步 | 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战略选择研究
产业技术进步 | 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战略选择研究



















 登录
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