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录
快速导航-

星青年 | 时间的洞穴(组诗)
星青年 | 时间的洞穴(组诗)
-
星青年 | 他们让云在半山腰吃草(组诗)
星青年 | 他们让云在半山腰吃草(组诗)
-
星青年 | 航迹(组诗)
星青年 | 航迹(组诗)
-
星青年 | 屠豚记(组诗)
星青年 | 屠豚记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存在与问道(组诗)
文本内外 | 存在与问道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仰望星空及其他
文本内外 | 仰望星空及其他
-
文本内外 | 雪暴露了万物突出的部分(组诗)
文本内外 | 雪暴露了万物突出的部分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无法回避
文本内外 | 无法回避
-
星现实 | 真正的声音(组诗)
星现实 | 真正的声音(组诗)
-
星现实 | 石锁飞舞(组诗)
星现实 | 石锁飞舞(组诗)
-
星现实 | 汉阳记忆(组诗)
星现实 | 汉阳记忆(组诗)
-
星现实 | 石谣(组诗)
星现实 | 石谣(组诗)
-
星现实 | 寻人启事(外一首)
星现实 | 寻人启事(外一首)
-
星现实 | 拿着钥匙的人(组诗)
星现实 | 拿着钥匙的人(组诗)
-
星现实 | 冷库工人(组诗)
星现实 | 冷库工人(组诗)
-
人间书 | 时间的脸谱(组诗)
人间书 | 时间的脸谱(组诗)
-
人间书 | 生命由此找到了着落(二首)
人间书 | 生命由此找到了着落(二首)
-
人间书 | 致母亲(组诗)
人间书 | 致母亲(组诗)
-
人间书 | 在雕像丛中(组诗)
人间书 | 在雕像丛中(组诗)
-
人间书 | 必然之诗(组诗)
人间书 | 必然之诗(组诗)
-
人间书 | 灯(三首)
人间书 | 灯(三首)
-
人间书 | 胡同(二首)
人间书 | 胡同(二首)
-
人间书 | 秋天,我可以把时间搬走(组诗)
人间书 | 秋天,我可以把时间搬走(组诗)
-
山河志 | 安静的深处(组诗)
山河志 | 安静的深处(组诗)
-
山河志 | 雪很大(组诗)
山河志 | 雪很大(组诗)
-
山河志 | 三行诗:与落叶有关(组诗)
山河志 | 三行诗:与落叶有关(组诗)
-
山河志 | 魏家山情诗抄(组诗)
山河志 | 魏家山情诗抄(组诗)
-
山河志 | 听琴图(外一首)
山河志 | 听琴图(外一首)
-
山河志 | 山居图(组诗)
山河志 | 山居图(组诗)
-
山河志 | 看 山(外一首)
山河志 | 看 山(外一首)
-
山河志 | 下一站是大海(组诗)
山河志 | 下一站是大海(组诗)
-
实力派 | 孤岛皮筏艇(组诗)
实力派 | 孤岛皮筏艇(组诗)
-
实力派 | 另一个伤口(外二首)
实力派 | 另一个伤口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简书(外二首)
实力派 | 简书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望星空(外二首)
实力派 | 望星空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开花就是了(组诗)
实力派 | 开花就是了(组诗)
-
实力派 | 漏掉的时光(组诗)
实力派 | 漏掉的时光(组诗)
-
压轴 | 纯真年代(组诗)
压轴 | 纯真年代(组诗)
-
星干线 | 偏岩古镇
星干线 | 偏岩古镇
-
星干线 | 钉下的内伤
星干线 | 钉下的内伤
-
星干线 | 河 流
星干线 | 河 流
-
星干线 | 石壶水墨
星干线 | 石壶水墨
-
星干线 | 菜
星干线 | 菜
-
星干线 | 小确幸(外一首)
星干线 | 小确幸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把青葙指给你看
星干线 | 把青葙指给你看
-
星干线 | 玻璃的隐痛
星干线 | 玻璃的隐痛
-
星干线 | 光的算术(二首)
星干线 | 光的算术(二首)
-
星干线 | 信笺
星干线 | 信笺
-
星干线 | 昆虫旅馆,兼致之雅
星干线 | 昆虫旅馆,兼致之雅
-
星干线 | 外 婆
星干线 | 外 婆
-
星干线 | 立 春(外一首)
星干线 | 立 春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火车一直在疾驰
星干线 | 火车一直在疾驰
-
星干线 | 假日办公楼
星干线 | 假日办公楼
-
星干线 | 孤山之中山公园
星干线 | 孤山之中山公园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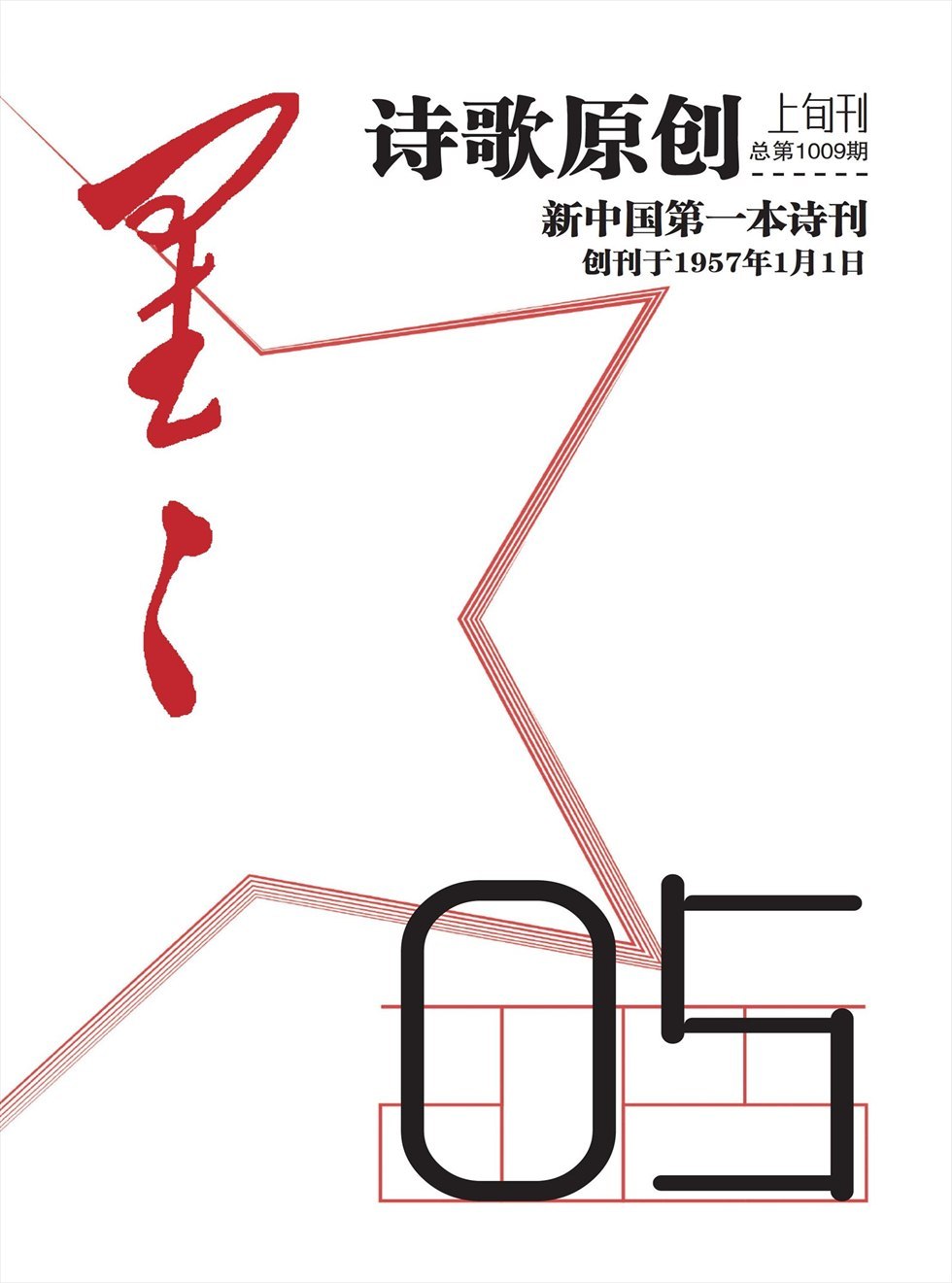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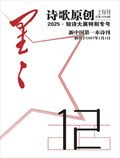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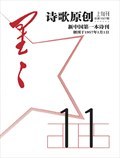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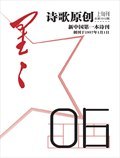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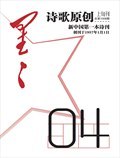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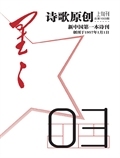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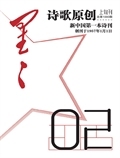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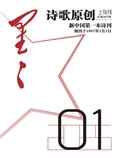









 登录
登录